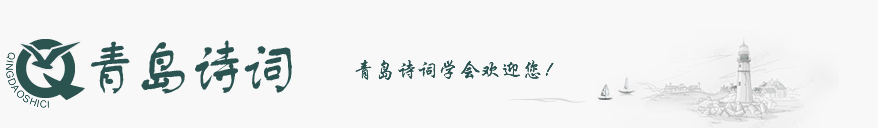象、情、意 ----读两首诗试谈诗家语的基本要素及其艺术结构
诗词是语言艺术,是诗词创作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古今说法很多,觉得莫过于“诗家语”说得透彻、管用。
周振甫在他的《诗词例话》<诗家语>中说:“《诗人玉屑》卷六里面提到王安石说的‘诗家语’……可以体会到诗家语的好处。第一,体会到诗的含蓄。……第二,体会到诗要突出形象。……透过形象来写情思。”这两点好处,准确揭示出诗家语中三个基本要素:“形象”、“情思”即感情、用意。 为行文方便,我把它简称为:象、情、意。周振甫在<诗家语>中还说:“像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提前写茅店是为把它突出来,透露出作者对它是有感情的。”这种化实为虚的艺术手法,便是诗家语的艺术结构。我从自己诗词创作实践中体会到,上述诗家语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基本要素和艺术结构这两个方面。在创作中,如果准确把握和运用好诗家语这两个方面,便可得心应手地写出好诗词。
下面请允许我借用当今两首诗来谈一谈这方面的体会。
在2011年中华诗词学会举办的“扬州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全国诗书画大赛中,湖北作者徐绪明的《鹧鸪天·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感怀》:“合是梅花清秀姿,生来不怕雪霜欺。一从亮相南湖后,九十年来放愈奇。勤管理,莫松弛,务防虫蛀干和枝。植根大地春长驻,花俏花香无尽时。”这首词以高票获得了诗词一等奖。这首词,首先是形象鲜明。前人写梅花的诗词很多,如陆游《卜算子·咏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赞颂梅花的高洁,写出他坚决不肯与主和派同流合污的劲节。毛泽东的同题词则“反其意而用之”:”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写出了一个自信、自豪、自然的革命家性格。这首词则是以梅花比喻党的品格:“合是梅花清秀姿,生来不怕雪霜欺。”使我们会立刻想到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能很快领会得这句里蕴涵着的战斗的独特的情思,见到“不怕”品格的鲜明形象。二是情感真挚。尤其是第三句“勤管理,莫松弛,务防虫蛀干和枝。”读者自然会联想到当今的反腐败,是忠告,是警示,充分表达出人民大众对于党的诚挚的感情。为什么说诗家语,这里的“家”,格外体现出诗人对于所写对象真实的情感。清代学者焦循在其《毛诗补疏序》中说:诗“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庄子·渔夫》中指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三是用意精深。特别是末句:“植根大地春长驻,花俏花香无尽时。”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赞颂和衷心的期待。而这种“春长驻”,“无尽时”之意,含蓄在“植根大地”、“花俏花香”里,让读者去思而得之。思即意,这便是诗家语的意。北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四是下语平淡。这首诗皆为寻常语,却句句是诗家语。我们常说口头语可以入诗,是说可以,入诗得要提升为诗家语。平淡不是浅薄。平淡的诗家语,是具有真象、真情、真意鲜活生命力的。纸上得来终觉浅,得要深入生活。现实生活中,才有鲜活的象、情、意的平淡语。灵感从哪里来?生活。灵感是象、情、意三者的妙合,并不神秘。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诗家语,高于口头语。书本上已有的,即使是自己已有的,都不鲜活,必须是此时此地,才见真,才能打动人心。聂绀弩先生说:“吾生俯拾皆传句,那有工夫学古人。”元稹称颂杜甫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巴金先生写给1980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致辞中的一段话:“我始终相信那句老话:生活培养作家。”袁枚《随园诗话》中说:“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求其精深,是一半功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功夫,非精深不能超超独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领解。”
诗家语三个基本要素,如同自然界的生物,阳光、空气、水份三者一个也不能少。形象鲜明、情感真挚、用意精深、下语平淡,乃诗家语的基本。这首词的好,好就好在句句都是诗家语,不是那种纯概念的说理或直抒胸臆的抒情,而是由象、情、意三个基本要素化合而成的。我曾以《把握诗词三要素的结构、运用与追求试谈中华诗词的普及与提高》(载《诗词世界》2016.8.78-80页)为题谈过,之所以说基本,源自三个基本立论:《周易·系辞》中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的象,是物象。唐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根情”,这里的情,是感情。诗人艾青说:“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浅露的语言表达出来,才是最理想的。”“深厚博大的思想”,就是用意。
这首词各句诗家语的艺术结构,也是别具特色的。“一从亮相南湖后”,是联想,想象,是虚笔;“九十年来放愈奇”,是实笔。化实为虚,以虚显实,虚实相生,由梅花意象,组合引发生成“南湖”红船,“放愈奇”的诗家语的意境。从虚实相生这一内在结构特征看出,诗家语是由两个部分组合而成,一是基本要素,即意象;二是艺术结构,即意境。简单说来,诗家语的组合是意象加意境。北大袁行霈教授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中说:“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达是: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漂浮于天上的云。云是由水珠聚集而成的,但水珠一旦聚集为云,则有了云的千姿百态。”(见《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下面来读樊玉媛《学诗小记》(载《中华诗词学会通讯》2018年第3期54页)中<看丁老改诗>的原诗和改诗。题目是《打开电脑看家乡》。原诗是:“轻击键盘输吕梁,鼠标一点到汾阳。边山果木核桃旺,盆地高粱谷子黄。城镇园林遮旧貌,乡村街院换新装。神泉美酒商工贸,万象和谐奔小康。”为节省篇幅,专谈末句。此原句末句正如《学诗小记》中所说:“写了‘和谐’,写了‘奔小康’。而丁老认为这些政治口号、套话、熟语恰恰是诗之败笔,脱离了全诗的情境,走向了概念化、公式化。”一句话,非诗家语。改诗则全然不同。改诗是:“轻击键盘赴吕梁,鼠标一点到汾阳。边山枣木胡桃旺,坡底高梁谷子黄。城镇园林荫旧貌,乡村街院焕新装。神泉酒沃游人梦,驭电朝朝回故乡。”改诗末句亦如所说:“‘游人’是作者自指,‘沃’是动词,浇沃之意。家乡美酒浇沃了他这游子的梦,使他更加思念故乡,因此,他便天天通过电脑回故乡了。‘驭电’是熟语,读者一看便知是使用了电脑。在电脑上天天可以看家乡——‘朝朝回故乡’既点了题,回应了开篇首句,使全诗有了完整感,又扩大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尾句一虚,全诗皆活。”一句话,诗家语也。
当今诗词创作,需要诗家语;诗家语,也需要诗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