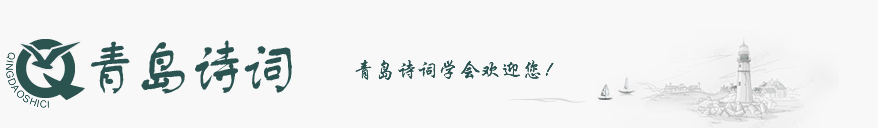叶嘉莹: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一)
在开始正文以前,首先我要说明在标题中所用的“懂”与“解”两个字,实在并无深意,“懂”就是明白、懂得的意思,“解”则是分析、解说的意思。我之取用了这一个标题,完全只是因我教书二十多年以来一点甘苦自得的体验而发。根据个人的教书经验,我以为诗可以分做四类。其一是易懂也易解的诗,如元稹的《上阳白发人》、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这些诗不仅在字面上没有生字难词,可以使“老妪都解”,就是在内容方面,对其所吟咏的情事,也是不难加以明白确指极易解说的,这一类诗我们姑且把其艺术价值置而不论,至少以教书而言,我以为乃是最为容易讲解的一类诗。其二则是难懂而易解的诗,如韩愈的《南山》诗,卢全的《月蚀》诗,这些诗中充满了难字怪句,看起来非常难懂,要讲这些诗,一定要费许多时间为那些生难的字句翻检字典和辞书,可是在内容方面则并无什么深意可资探寻和解说,这一类诗也许有某一些对奇险有偏好的读者会认为也不失为艺术上另一方面之尝试和成就,但就我个人而言,总以为讲这一类诗费力甚多而所得甚少,好像颇不合算的样子。其三则是难懂也难解的诗,如李白的《远别离》、李商隐的《燕台》诗,这些诗不仅在字句方面一看就使人觉得闪怪变幻难于把捉,讲解起来更是情思幽邈,众说纷纭,使人难以明言其意旨之究竟何在,这在教书而言,是很难解的一类诗,然而寻幽探奇虽艰难曲折也自仍有其一份乐趣在,以我个人而言,对这一类诗是颇有着一些偏爱的。其四则是易懂而难解的诗,这一类诗,我以为也可以分别为两种,从字面之明白浅显言,其使人易懂虽是一样的,可是在内容方面使人难解的原因就不尽相同了。一种使人难解的原因是由于内容所蕴蓄的深远幽微,使人难以为其意蕴加以界说,则读者纵使颇有会心,也难以言语来解说表达,如陶渊明《饮酒》诗“结庐在人境”一首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以为代表;又一种使人难解的原因则是由于语意与语法的含混不清,造成一种模棱两可的现象,使人难以确指其含意究竟何在,如李后主《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一首之末两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天上人间”四字可以为代表。这两种易懂而难解的诗,都是看似浅明,而极难解说的,而以艺术价值言则这一类易懂而难解的诗往往有极高的成就,因为这一类诗以表现而言其写作态度往往最为真挚诚恳,丝毫没有逞强立异争新取胜的用心,而意蕴方面则又深微丰美使人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受,《论语》有言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是很值得我们研赏的一类诗,因此我很想为这一类诗寻出一种解说上的基本原则来,这是我所以要想选择一组易懂而难解的诗来加以解说的缘故。当然我原可以作自由之选择,如前所举之渊明诗及后主词都可作为此一类诗之例证来加以分析解说,然而我现在所选取的则是较之渊明诗和后主词都年代更早也更有系列的一组诗,因为我以为这一组诗同时可以代表前面所举的易懂难解之诗的两种类型,无论在内容之深微丰美及语意之含混模棱方面,都值得我们将之作为例证来加以讨论分析,这一组诗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向被人目为评价最为高卓而解说也最为纷纭的一组诗——《古诗十九首》。
关于《古诗十九首》之时代与作者的问题,自齐梁以来早就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因此在本文中不拟再加赘述,而且,这一方面的考证也不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总之,我以为这十九首诗乃是东汉之世的作品,作者虽时代相近却并非一人,其姓名也早已不可且不必确指,而各诗所咏之内容,也并无一定之次序,更无任何关联或一贯性之可言,然而如果以艺术价值来衡量,则这十九首诗却又确实有着艺术境界上某种成就之一致性。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我以为诗人所写之内容,就其深浅广狭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共相的,一类是属于个相的。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后主词云:“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有人从字面上来吹求,说后主既非宗教家,又本无救世救人之意,如何可以将之比作释迦基督?又如何能说他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实这是误会了王国维的本意,王氏的本意只是以释迦基督来作一种借比,他的本意乃是说后主所写的词好像能写出千古人类所共有的某种悲哀,而道君皇帝所写的则只是一己小我个人之悲哀而已。如道君皇帝之《燕山亭》词,他所写的“裁剪冰绡,轻叠数重……院落凄凉,几番春暮……万水千山,故宫何处”,似乎都只是属于个相的外表的事迹,而后主《虞美人》词所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与《乌夜啼》词所写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则是所有有情之人所共有的伤今怀往的哀伤,与所有有生之物所共有的生命无常的慨叹,也就是说后主所写的情意境界乃属于共相的。其所以能呈现为人类情感上之某种共相,我以为乃是由于他能写出人类感情活动的某种基型的缘故。而且这种感情往往乃是人所同具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感情。以《古诗十九首》而言,其所以能享有千古常新的高卓之评价者,也就正因为它们所写的乃是千古常新的人类最根本的感情之基型的缘故。虽然《古诗十九首》之内容并不尽同,但无论其所写的是离别的怀思,无常的感慨,或是失志的悲哀,总之它们所表现的乃是人类心灵深处最普遍也最深刻的几种感情上的基型。因此在意蕴方面,这十九首诗可以说得上是经得起千古所有人类的无尽的发掘,而都能对之引起共鸣的,而意蕴愈普遍深微的作品,也就愈难以外表肤浅的事迹来加以解说界定。这种意蕴当然与渊明诗的“此中有真意”并不相同,因为十九首所写的乃是人与人间感情的共相,而渊明诗所写的“真意”则是人与自然间精神的交融,其内容当然不同,然而由于意蕴之难以界定,而使读者对之感到易懂而难解的一点则是相同的。这是欣赏《古诗十九首》所当具有的第一点认识。
其次再就语法与语意之含混模棱而言,西方文学批评界对这方面之研究已经建有相当之体系,最著名的如威廉·恩普逊(William Empson)所著之《七种暧昧的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他把诗歌的语意与语法之含混模棱的现象标举出七种暧昧的类型,最近哈佛大学的梅祖麟先生也曾因恩氏之启发而写了一篇分析中国诗的文章,标题为《文法与诗中的模棱》,文中曾分七节来讨论唐诗律绝中的模棱与假平行的各种现象。其实无论东方或西方的诗歌中都有此种含混模棱的现象,而且其语意与语法的变化甚多,很难以少数几种类型来归类,但是承认诗歌中可能有此种含混模棱之现象的存在,此一认识则是极为重要的,而且此种现象往往也正是造成一篇伟大作品的重要因素。因为正是这种含混模棱的语意与语法,有时却使得作者与读者之意念的活动范畴都更加深广丰富起来。传统的批评界一向缺乏此种认识,因此传统的批评总是想努力把一首诗加以最为拘限的界说,而且各是其所是,对一切不合一己之见的说法都妄加排斥,这是一件极可憾惜的事。我以前曾写过一本《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从这本书中所收集的资料,就可看出在三十五种不同的注本中,对杜甫这八首诗有着何等纷纭歧异的解说,而综合起来一看,就会发现这种种不同的解说在杜甫诗句中原来都有着相当的可能性,而如果想要择一固执把其他说法都一概抹杀,则反而是愚拙而浅薄的看法了。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在对诗歌加以解说时,就可以有若干方便,而不会再犯固执拘限的毛病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诗歌中含混模棱的现象,变化甚多,如果就其外表来归类,乃是一件极为烦琐的事,但如果从其根本的来源来归类,就简单得多了。我以为诗歌之所以引起含混模棱的现象可以有三种因素:其一,由于表现的工具——文句的读法与语义所能引起的解释之分歧;其二,由于表现的内容——作者心中之意识的活动之难以确指;其三,由于表现的效果——读者心中所引起的感受与联想之反应的不同。我在前面所举的后主词之“天上人间”一句,其所以引起含混模棱之现象,主要乃是因为语法之不够完备,因为这一句中的四个字,实在只有两个名词,一个是“天上”,一个是“人间”,要想加以解说,势必要在这两个名词之外,更加以若干补足的述语,这些述语如何加在上面,当然就未免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了。至于《古诗十九首》之所以造成若干含混模棱的现象,则分别具有前面所说的三种因素,有时且是两种或三种因素的混合,因此承认这些含混模棱的现象,乃是欣赏《古诗十九首》所当具有的另一点认识。
前面我曾说过《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然而在艺术价值上,却有着某种成就之一致性,其成就即在于从内容方面而言,其意蕴之深微普遍既最近于人类感情方面的几种最根本的基型;而从表现方面而言,其语意与语法之含混模棱,又最为丰美而富于变化,因此《古诗十九首》的文字虽极为简单平易,而所引起的解释则是人各一辞,异说纷纭,这正是一组最可作为代表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自齐梁以来,对这十九首诗加以评注解说的著作已有很多,除了对作者及时代的考据之说不算以外,对于内容方面的解说大抵是想对之从外表的事迹来加以界定者多,而从感情之基型来加以推演者少,现在就让我们试从一个新角度兼采各家之说,从多种解说之歧义中来对其所蕴涵之感情的基型一作探寻的工作。在此有一点我必须声明的,就是此文并非考证专著,因此除了特殊的解说我标明了出处以外,至于一般性的解说,为了避免烦琐,我并未一一注明出处,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下面即以《行行重行行》为例,来解说《古诗十九首》之易懂而难解。先抄录全诗如下: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首诗当然一望而知乃是一首写离别之情的诗,昔江淹《别赋》有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别情正是一般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感情经验,虽为人类共有之情,其表现于诗歌之作品中却也仍有着共相与个相之不同。例如柳永《夜半乐》词之“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其别情就是属于个相的;而此一首古诗所写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其别情则是属于共相的。属于个相的作品,对于时间、空间与夫事迹、人物,大概都有着比较可以界定的叙述,如前所举的柳永之《夜半乐》一词,我们可以从“冻云”一句知其时节,从“江渚”一句知其地点,从“扁舟”一句知其为水路而非陆路,从“绣阁轻抛”数句知其为远行人之口吻而非送行人之口吻,为男子之口吻而非女子之口吻。可是现在我们所要研究的这一首“行行重行行”的古诗则不然了,这一首诗不仅没有写出明确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连它是远行人的口吻,是男子之口吻或女子之口吻,亦复难于确定,因此历代解说这首诗的人也就有了纷纭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是逐臣之辞,有人以为是弃妇之辞,有人以为是行者欲返而不得之辞,有人以为是居者怀人而不见之辞,如果把这首古诗与柳永的那首《夜半乐》词相较,则柳永那首词对读者所能唤起的共鸣乃是有限的,而这一首《行行重行行》的古诗所能唤起的共鸣则是无限的,那就因为这首古诗所写的不是外表的个相,而是人类心灵中之某种情感活动之共有的基型的缘故。因此,时无分古今,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事无分远行与送行,遂都被包容于此种基型之中,而同被其感动而唤起共鸣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十九首云“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就正是因为这一种道理。如果以为这一首诗之多歧解是它的短处或者妄想要固执一端而蔑弃其他的说法,那就未免浅之乎视此诗,同时也就不能体会这首诗的真正的好处所在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