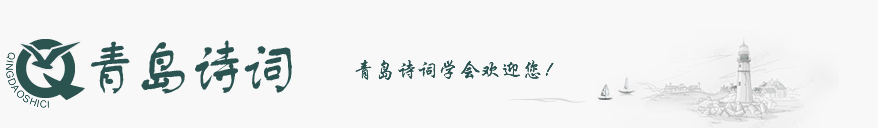叶嘉莹: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二)
现在我们先从第一句“行行重行行”看起。这一句五个字全用平声,如果绳之以后世声律之说的四声八病的限制,则这一句诗竟可以说是通身是病了,然而我们读起来不但未尝觉得有任何违拗哑涩之感,反而觉得就恰好正是这五个字才真正写出了我们离别之时所共有的一份感觉和声音。而我们试一分析就会发现原来这五个字中乃竟有四个字是相同的,其实这一句诗原来就只是“行行”一个叠字动词的重复,中间一个“重”字也只不过是点明此一重复之动态的字样而已,所以这五个字在意象上,所呈现的原来就是一片基本的离别的动态,而且无论以远行人而言,以送行人而言,都是同样真实的。从远行人而言,渐行渐远,当然是“行行重行行”;从送行人而言,则目送去者之渐远,其动态也依然是“行行重行行”,何况这五个字除了意象上呈现着一片离别之基本动态而外,声音上的五个平声字,所予人的也一样是一逝不返、有去无还的感觉。而这五个字又何其简单何其平易,何其朴质而自然,完全没有丝毫安排雕饰的用意存在于其间,昔《庄子》有“天籁”、“人籁”之说,如果说后世声律谨严的有心用意之作是“人籁”,则这五个字就正近于所谓“天籁”了。
次句之“与君生别离”也是一句极平易的句子,却写出了千年万世之人所共有的离别的哀伤,昔《楚辞·九歌》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杜甫《梦李白》诗亦有句云:“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在人世间我们所经历的最普遍最不可避免的悲苦莫过于离别,而离别又可分为“死别”与“生离”两种。观夫《楚辞·九歌》及杜甫《梦李白》诗所写的当然都是与“死别”相对的“生离”。生离之所以异于死别,或者说生离之悲苦之所以更甚于死别者,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点来说:第一,死别之形成乃是不由人的一件事。对于这种无可挽回的生命的终结,我们虽然有着极怨深悲,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有着莫可奈何而只好一意担荷承受的死心塌地的感觉。第二,死别乃是另一对象的完全消逝,当此事初一发生时,感情之另一端骤然落空,我们自然极感痛苦,然而日往月来,天长岁久,没有对象的怀念,自然也就会因其另一端之落空而渐趋淡忘了。至于生别则不然。第一,生别乃是可以由人的一件事,如果相爱之二人,其中一人之生命已不复存在,那当然无话可说,如果二人都同时仍存在于人世,那么同时存在于人世的两个相爱的生命,为什么竟然不能同居共处,而要造成离别的悲苦呢?这是生别较之死别使人更觉有所不甘的一点;再者,生别的对象并未自人间消逝,只要所爱之对象一日尚在于人间,则二人重见的希望,便一日不甘弃舍,如此则有生之年尽是相思之日。死别是顿断之后逐渐可以放开的,而生别则是永无断绝的悬念怀思,这是生别较之死别使人更觉难于舍弃的又一点。证之于《红楼梦》中宝钗把黛玉之死告诉宝玉使之一恸决绝,然后可以安心养病的话,则生别较之死别之更为不甘,更为难舍,当属可信。然后再回头来看这一句古诗,“与君生别离”,“与君”二字是何等亲切的关系,“生别离”三字又是何等无奈的口吻,其不甘与难舍之情岂不跃然纸上?而除此之外“生别离”三字还更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不把“生”字看做与“死”对举的死别生离之意,而把“生”字解释做“硬生生”的“生”字之意,如马致远《汉宫秋》剧之“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及《雍熙乐府》无名氏《端正好》赶苏卿一套之“本是对美甘甘锦堂欢,生扭做悲切切阳关怨”,便都是把“生”字做“硬生生”的意思来用的。如按此意,则“与君生别离”一句,乃是说我与你硬生生被别离所拆散之意,似乎也更有着一种激动强烈的不甘之感,所以吴淇之《古诗十九首定论》就采用此一解释说:“生字当解做生熟之生,犹云生生未当别离而别离也。”这种解说未尝不好,只是我们不要忘记十九首乃是汉代的诗,而“生”字之被用做“硬生生”的意思,则似乎乃是唐宋以后的事,所以此句“生别离”三字,当然仍以其他注家所采用的《楚辞》之“生别离”的解释,指死别生离之意为是。而将之解做“硬生生”之意,则只是后世读者之一种联想而已。然而就文学之欣赏而言,则此种联想可以使原诗之意境更为丰富多彩,则也未始不可承认其可以有此一种想法和感受的存在。
接下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四句,则是从临分手时的“生别离”之深悲极苦的感情中一路接写下去,一句较之一句为遥远,一句较之一句为绝望。从渐行渐远的日益加长的万里距离,到天涯阻隔、人各一方的清醒的认知,然后因此种认知再转回头来更作重逢会面的遥想,才发现中间的阻隔竟然已经是无法迈越的了,这里的“道路阻且长”一句,“阻”字是一层隔绝,“长”字是又一层隔绝,如果路虽险阻而并不遥远,那么以一个有情之人,也许终能胜过险阻而达成见面之望,或者路虽遥远而并不险阻,那么只要有见面的决心,也必能跨越长远的距离而有相逢之一日;然而在此处所说的既“阻”且“长”的双重隔绝之下,则纵使是一位有情之人,而人力微弱,年命几何,于是而重逢再见的希冀乃终于落入于绝望的地步,所以乃有以下“会面安可知”一句的充满相思之苦与绝望之悲的哀吟叹息。这四句诗,无论对行者而言,或对居者而言,其哀伤之情都是同样真实也同样使人感动的,这便因为此四句所写的由离别而造成的距离与怀想,也正是千古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感情之基型的缘故。
下面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则于抒情叙事的绝望哀吟中,突然荡开笔墨,插入了两句从表面看来与上下文似都不相连贯的比喻。这种写法乃是古诗及汉魏乐府的一种特色,如《饮马长城窟行》之“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一首,也是一路叙写离别相思之苦地写下来,然后突然于抒情叙事的半途中骤然停顿,而接上去“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望之与上下文似皆不相衔接的比喻,全不作指实的说明,因之乃可使读者生多方面的联想,作多方面的解释,于是而使前面所叙写的情事蓦然都有了回旋起舞的一片空灵之感。这是文学创作中极高的一种手法。而尤其可贵者则在于古诗乐府的此种比喻多半所取材的都是人世间某种极自然之现象,如《饮马长城窟行》之“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及这一首古诗之“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都只是大自然界的某一种不假人力、不假思索而本然原有的自然现象,以这种现象来作比喻,姑不论其所比喻的意思究竟何指,总之,在直觉上已经先能予读者一种恍如定命的无可奈何的必然之感了。而另一方面此种比喻又可由多方面之联想作多方面的解释,这是极深刻极丰美同时又极自然极质朴的一种比喻手法。“枯桑”两句,因为并非本文所要讨论,姑置不谈。现在我们只看这一首古诗的“胡马”两句,这两句比喻虽极自然简明,然而其所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则是极为丰富的。我们先从这两句的出处来看,就可以分为两种不同之喻意。其一李善《文选》注引《韩诗外传》云:“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而这“不忘本”的意思,则又可以分做不同的两方面来看:如果从行者的一面来看,则此两句当然乃是正面写远行之人的不忘本的思乡念旧之怀思;而如果从居者的一面来看,则此两句乃是反面的喻意,谓胡马尚且向北风而依恋,越鸟亦且向南枝而巢宿,物皆怀旧,则彼游子岂不思乡乎?这是采用《韩诗外传》为说所可能引起的两种解释。其二《吴越春秋》亦有“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之言,则乃是取用“云从龙,风从虎”的一种同类相求的用意,如用此说,则此两句诗乃是写凡物皆有其所相依而不忍离去的归附,所以胡马尚依北风越鸟亦巢南枝,然而我与君乃是同心相爱之人,如何乃竟然别离至如此之久远而不能互相依投归属乎?这是一种解说。而除了此两种“不忘本”及“同类相求”的取意以外,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把上面的两种出处及取意都抛开不论,而只从字面来看,则胡马与越鸟,一北一南,所予人的也自有一种南北睽违的隔绝的直感。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引纪昀曰:“此以一南一北申足‘各在天一涯’意以起下相去之远”,就是从这两句一南一北之睽隔的直感来作解说的,只是纪昀却想以这一种说法抹杀其他的各种解说,谓“ ‘胡马’二句有两出处,一出《韩诗外传》,即善所引不忘本之意也;一出《吴越春秋》……同类相亲之意也,皆与此诗意别,注家引彼解此遂致文意窒碍”。这种固执一端的说法,就未免过于狭隘了。总之,此两句比喻所予读者之意象极为简明真切,有一份命定的必然之感,而其所可能引起之联想却又极为丰富变化,有行人念旧之思,有居人对行人不念旧之怨,有相爱之人不得相依共处的哀愁,有南北睽违永相阻绝的悲慨。而从表面看来,则又是与上下文全然不相衔接的两句突来之喻象,使全诗至此忽然起了一阵回旋动荡的姿致,却又同时有承转变化的许多妙用。这真是神来之笔的两句好诗。
下面“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两句,则从回旋动荡之悬空的比喻中,又返跌回真真切切的现实来。是则无论前两句“胡马”及“北风”之取喻为何,纵使有不忘本之心,纵使有同类相亲之愿,纵使有不甘睽违的悲慨,总之,“相去日远”、“衣带日缓”乃是相离别以后之无可挽赎的事实。这一返跌原来就极为有力而且惊心,而又遥遥与前面“相去万余里”数句呼应承接,更且不避重复地同样用了“相去”两个字,但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从重复之中更转进一层的写法。我们试把此同以“相去”二字为开端的两句一作比较,就会发现这两句的情意在予读者的感受上,实在有许多不同“万里”一句虽亦有相去甚远之感,但一则“万里”所代表的只是空间,并无时间之含义,再则“万里”之“万”字虽然是个极大的数目字,但毕竟仍是个有限的数字,而此句之“日已远”三个字,则其所表现的乃是除空间以外更兼有时间的双重的悲感。前一句只写空间,则万里虽远,相见未始无期;而此句之“日已远”,则以时间与空间相乘积,是则时间之久既属无期,而空间之远又更为无尽。而此句之尤妙者更在其不仅以“相去”二字与“万里”一句相呼应,更且以“日已”二字与下一句相排偶,于是从“相去日已远”到“衣带日已缓”,离人乃在时空的双重乘积下造成了相思与憔悴的同样无尽无期。柳永《凤栖梧》词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大似自此句蜕变而出,只是柳永的两句词似尚不免用力着迹,虽曰“终不悔”,但毕竟已将“悔”字明白说出,则已隐然有计较之念,而此句之“日已”两个字则只是日复一日的一往无还的刻骨相思,虽然至于憔悴消瘦也依然毫无回顾,而外表所写的则只是衣带日缓一件事实而已。无论就行者或居者而言,如此深刻坚毅的感情,如此温柔平易的表现,也都是足以使人感动的。
而就在这种使人感动的绵长久远的相思之悲苦中,下面却忽然承接了“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十个字,我以为这是这一篇诗中最使人摧毁伤痛的所在。我们从开端的“生别离”“天一涯”读下来,一直读到前一句之“相去日远”“衣带日缓”,都使人觉得诗中人物虽有离别之痛,然而隔绝的只是时间与空间,至于二人之间相信爱的情意则是毫无阻隔的,如此则相去虽远相别虽久,而相思之感情永在,相见之信念长存,则虽在别离之悲苦中,也依然有着一份安慰和支持的力量,至此忽然以“浮云蔽白日”一句,使一片沉重的阴影当头笼罩下来,这真是何等难以承受的重击。只是这句诗的浮云究竟何指呢?而且被蒙蔽的又究竟是哪一方呢?李善《文选》注云:“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亦云:“浮云比谗间之人。”是“浮云”乃指二人中间的谗毁蒙蔽,这一点在传统的注解上是相同的,至于被蒙蔽的是哪一方,则就有不同的说法了。一种是把被蒙蔽的“白日”比作被放逐的贤臣,也就是下一句的“游子”,李善注引陆贾《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彰日月”,以“蔽贤”与“彰日月”对举,则日月之所喻当然乃指贤臣而言,是以吴淇之《古诗十九首定论》及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就都指明说“白日比游子”。而另一种说法则是把被蒙蔽的“白日”比作君王,饶学斌《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就采用此一说法,谓:“夫日者,君象也,浮云蔽日所谓公正之不容也,邪曲之害正也,谗毁之蔽明也。”这两种说法虽不尽同,但把这首诗都看做乃是贤臣被放逐且遭谗毁而作,则是一样的。此外还更有另一说法,就是把这首诗看做乃是思妇之辞,张玉谷《古诗十九首赏析》即云:“此思妇之诗……浮云蔽日,喻有所惑,游不顾返,点出负心。”是“白日”乃指游子,“浮云”则指游子在外面所遇到的诱惑。只是一个遇到诱惑就薄幸不归的游子,既不是君王,又不是被放逐而依旧忠心耿耿的贤臣,为什么仍然以光明的“白日”为其象喻呢?于是乃又有人以为白日乃是象喻游子旧日温暖的情爱之光照,于今情爱隔绝所以说浮云蔽日也,方东树《论古诗十九首》就采用此说,云:“白日以喻游子,云蔽言不见照也。”看到前面这些说法,我们已经知道,这两句诗所能引起的解说是何等歧异纷纭,但我以为其间仍然可以归纳出一个根本的基型来,那就是“白日”乃是任何一种圆美光明的情操之象喻,而浮云则是一片蒙蔽的阴影,无论是君臣、夫妇、朋友,最可悲哀的都莫过于当彼此经过悠久而漫长的时空之离别以后,而其中竟然有一方面有了一片隔绝蒙蔽的阴影,这乃是天地间最可憾恨的一件事。李义山有诗云:“不辞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我以为义山所写的这一种“暗”之蒙蔽与“断”之隔绝的悲恨,就与“浮云”一句大为相似。原来人世间最可哀痛的,不是年芳的零落,不是人寿的无常,而是被流尘所遮暗的一蕊光明,被天风所吹断的一缕芳香,于是在这种蒙蔽的阴影下,遂终于逼出了“游子不顾返”的痛心的结果,“游子”无论是被放的逐臣,或者是弃家的荡子,总之乃是离乡别井的远游之人,“不顾返”者则当是不更念及归返之意,然而离乡的游子何以乃竟然不更念及还乡呢?这一句仍然可以从两方面来立说。如果从行者方面而言,则本身就是游子,证之于这首诗前面所写的“生别离”的悲哀,及“胡马”、“越鸟”的不忘本的托喻与夫“衣带日缓”的憔悴相思,则游子之思乡欲返的深衷岂不显然可见?然而如今却竟然落到了“不顾返”的下场,环境有时可以逼使一个人作出与自己本心大相违背的决定,这是可伤痛之一,而且证之于下面所写的“思君令人老”诸句,则其欲返之本心实在又常存未泯,这是可伤痛之二,而此处却依然明明白白地写下了“不顾返”三个字,则上句“浮云蔽日”的阴影所造成的蒙蔽隔绝之使人战悸悲哀也可以想见了。再者此句如就居者方面而言,则“游子”便非自称而系称人之辞,“游子不顾返”者,思妇多情,而游子薄幸,这正是中国诗词中女性的传统悲剧。而中国女性传统的典型,一向都具有着人类含蓄隐忍这一方面的最高的情操,以最温柔的心来负荷最深重的伤害和哀愁,而且要做到无怨无怒的地步,所以此句也只说“不顾返”,而不是“不欲返”。如果是“不欲”则是游子已经决心不返,而“不顾”则似乎仍只是一时“不念及”之意,而且上一句的“浮云蔽日”把“游子”依然比作“白日”,是此一心目中之偶像,其光明温暖的圆美之象喻乃依然丝毫未改。然而虽有此温柔婉转的相谅之心,而“白日”毕竟已遭蒙蔽,“游子”亦竟然去而不返,反复思量,千回百转,在已遭蒙蔽隔绝的阴影下,所隐蓄的一缕相思之情的颤栗,是极为可伤的。
下面接以“思君令人老”一句,如果就居者方面而言,则在游子不返的情形下,而居者相思不已,那么“思君令人老”当然是极自然的承接。但如果就行者方面而言,则本身就是不返的游子,何以又说“思君令人老”呢?对此我想颇可以牵附韦庄的几首《菩萨蛮》词来为之立说。韦庄的《菩萨蛮》词一共有五首,有人认为乃是韦庄入蜀后之作,有人则以为乃是韦庄漂泊江南时所作。总之,这五首词写的乃是游子之情,则是可信的。假如我们按照传统的解说,把这五首词看做一系列的作品,那么,我们试看他如何从“红楼别夜”的“惆怅”写起,带着“早归家”的叮咛承诺,与“美人”“和泪”而“辞”,然而在别离之后,却一转而说出了“未老莫还乡”的话,再一转更说出了“白头誓不归”的话,而正当我们要相信游子之果然负心的时候,他最后却说出了“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的两句深情苦忆的呢喃。可见“不返”是一件事,而“思君”是一件事;“不返”可能是为了外在的某些不得已的因素,而“思君”则是本心中永难改变的初衷;惟其有前面“不返”的决绝之言,此处的“思君”才更有欲罢不能的真挚深刻之感,而且因“思君”而“令人”竟然至于“老”,则忧伤之深,岁月之久,皆可想见。然而相思的情意虽深,而已逝的年华不返,所以接着又说出了“岁月忽已晚”的五个使人惊心动魄的字来。无论就居者而言,无论就行者而言,既然有着不能斩断的“思君”之情,又有着无可避免的“人老”之痛,相见的日子无期,而相待的年华有限,岁月之晚,使人警觉于一旦无常来到,则所有相思相待的期望苦心都终将落空,这是何等使人不甘,又何等使人惊惧的一件事。所以说“岁月忽已晚”,“忽已”二字不仅写出了岁月的消逝迅速无情,更写出了相思之人对此岁月消逝的一份惊惧伤痛之感,何况前面已有过“人老”之言,则此处岁月之无情当然也就更为可哀了。
最后两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也是解说极为纷纭的两句诗。先说“弃捐”一句,“弃捐”二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解作被抛弃捐舍的意思,如班婕妤《怨歌行》所写的“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其“弃捐”二字便是此意;又一种则是解作丢开一边的意思,如乐府诗《妇病行》一首之“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其“弃置”一句之句法便与此“弃捐”一句之句法完全相同,是则此句之“弃捐”岂不可以解作彼句“弃置”之丢开一边之意。所谓“弃捐勿复道”者,按第一说乃谓这种被抛弃的悲哀不要再提了。如按第二说则乃谓把这事丢开一边,不要再提了。这两种说法实在颇为相近,而且皆归之于“勿复道”则是完全相同的,何以“勿复道”呢?一则言之无用,再则言之伤心,对于无可挽赎的事,除了一意承受之外,语言原是多余的事,这正是对悲苦体验得极深刻的话。至于末一句,“努力加餐饭”,则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把此句解作劝对方加餐之意,张玉谷《古诗十九首赏析》即云:“以不恨己之弃捐,惟愿彼之强饭收住,何等忠厚。”我以为此一说法乃是受了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一首“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数句之影响,以为此处之“努力加餐饭”也是书信中劝对方加餐的话,这种解说当然未始不可也未始不好,只是这样似乎就必须要把这首诗认做乃是书信的口吻才可以。又一种则是把此句看做乃是自劝之辞,姜任修《古诗十九首绎》云:“惟努力加餐保此身以待君子。”又引谭友夏云:“人知以此劝人此并以之自劝。”张庚《古诗十九首解》亦云:“且努力加餐,庶几留得颜色以冀他日会面也,其孤忠拳拳如此。”我以为承接着上面的“思君令人老”及“岁月忽已晚”读下来,则此处解作自劝之辞,实更为自然近情也更为深刻坚毅,因为在“人”之“老”与“岁”之“晚”的两重悲哀恐惧之下,要想坚持不放弃重逢再见的希望,则除了“努力加餐饭”之外,实在更没有其他可以延长生命胜过无常的方法;然而一个“衣带日缓”的人,每日在相思憔悴之中,要想加餐又何尝容易做到,所以上面才更加上了“努力”两个字,这两个字中充满了对于绝望的不甘与在绝望中强自挣扎支持的苦心,是将此句解作“自劝”较之将此句解作“劝人”为佳,则劝人加餐固然是忠厚之至,而自劝加餐则用情益苦,立意益坚,相思而必欲有相见之一日,乃甚至欲以人力之加餐胜过生命之无常,像这种为了坚持某一种希望,担荷起无量悲苦而勉力去做的挣扎支持,其所表现的已不仅是一种极深刻的感情,同时也是一种极高贵的德操。我常以为当一个人遇到悲苦挫伤之时,如果丝毫不作挣扎努力,便先尔自行败馁或甚至因失望与失败而自加戕贼,这样跌倒下去的人纵使能使人怜悯同情,也是不值得尊敬和效法的,反之,当一个人遇到悲苦挫伤之时,如果能自加勉力,在痛苦的挣扎中依然强自支持,则最后即使也终于失败而倒下去了,这样倒下去的人较之前者,才更富有悲剧感,更有波澜,更有力量,更有德操,更使人同情,也更使人尊敬,何况如果竟因艰苦之挣扎而居然有一日能使全心灵全生命所期待的事情终得实现,则岂不更是一件可欣喜礼赞的事!这一首古诗末两句所写的“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就隐然表现了这种最可贵的德操,同时言外之意更展现着一份无尽期的对重逢再见之深情苦待,而且与开端之“生别离”的哀痛遥相呼应,这种德操,无论对于居者或行者,无论是一个被放的逐臣或是一位被弃的思妇,或者是任何一个曾经过如此别离的悲哀与隔绝的痛苦而仍然一心抱着重逢的希望而不甘放弃的人,这首诗所写的情意都有着它永恒的真实性。这正是因为《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乃是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属于一种人类最普遍的感情之基型的缘故,而其语意与语法的含混模棱之现象则更造成了读者多种解说与感受的高度适应性,因此我们乃可以一方面掌握其情感的基型,一方面从多种不同的看法和感受来对之试加探触和解说,我以为这正是我们研赏这一类诗所颇可采用的一种态度和方法。
但是我最后仍要声明一句,就是我们所引用的说法虽然很多也并非丝毫无所别择,即以这一首《行行重行行》而言,有几个说法,就是我所不曾引用的,如饶学斌《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把这十九首诗全看做一人之作,云:“此遭谗被弃怜同患而遥深恋阙者之辞也,首节总冒,标‘会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二句为柱,自其三至其七为一截,承‘会面安可知’一柱而申之;自其二其八至其十六为一截,承‘思君令人老’一柱而申之;其十七收束思君,其十八收束思友,末以单收下截住。”他之所以要把此章《行行重行行》一首中之两句看做两根分别的支柱的缘故,实在因为他要把这十九首诗全解作逐臣被放思君恋阙之辞,而且又要认定是一人之作,但又发现有些首诗按照这一说法实在无法讲得通,因此遂又不得不加个“怜同病”的理由,把另一些诗勉强解作思友之辞。至于《行行重行行》一首何以又被分为两根支柱呢?他的解释是:“夫曰‘各’曰‘会面’曰‘南北’,此分谊相等,尔我同侪,直平等观者非可概之于尊长也,虽属愚氓,亦共知君父之尊……即不敢彼此平衡……此上截思友确是思友,断不得混作思君也。”又曰:“夫‘日’者君象也,‘浮云蔽日’……此孤臣孽子所自伤者也,而曰‘游子’曰‘思君’,明乎其为臣子也,此下截思君确是思君,断不得混作思友也。”像这样牵强比附任意割裂的说法,当然一望可知其为愚妄拘执,这是我们虽有心兼融众说,也无法采信的。又如,陈沆之《诗比兴笺》则按照《玉台新咏》的说法把这一首《行行重行行》及《西北有高楼》等八首都认为乃是枚乘之作,而且指明其写作之次序及时间事迹,云:“ ‘西北’、‘东城’二篇,皆上书谏吴时作,‘行行’、‘涉江’、‘青青’三篇则去吴避梁之时;‘兰若’、‘庭前’二篇则在梁闻吴反复说吴之时;‘迢迢’、‘明月’二篇则吴败后作也。”像这种把作品与作者之生平比附立说的方法,用之于某些确实可信的诗与作者之间也不过只能作一种讲诗的参考而已,尚不可率而便完全据以立说。何况这几首诗原来就不一定是枚乘的作品,而且其诗与诗之间及诗与枚乘的生平之间更看不出丝毫必然之关系,像这一类说法,正与前所举之月午楼的说法同样牵强拘执,这都是我们所无法勉强同意的,我在此不过略举两例以作说明而已。
(完结)